煤电行业为何仍占据中国电力结构主导地位?
尽管风光装机增速惊人,但煤电依旧提供超过60%的全社会发电量。核心原因有三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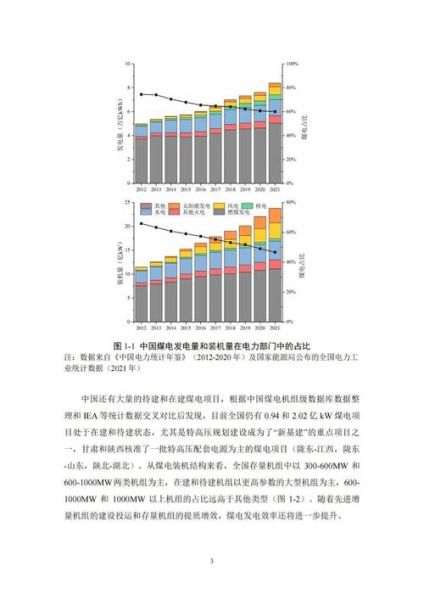
- 电网对稳定基荷的刚性需求,风光尚难全天候替代;
- 地方财政对煤炭产业链的税收依赖短期难以摆脱;
- 存量煤电机组平均服役年限仅12年,提前退役成本过高。
“双碳”目标下,煤电企业面临哪些真实约束?
政策端:2025年后,全国碳市场预计纳入全部煤电机组,配额缺口成本或达80~120元/吨CO₂。
市场端:2023年山东电力现货市场出现负电价时段,边际成本高企的煤电机组被迫倒贴发电。
金融端:五大行对新建煤电项目贷款利率已上浮50~80BP,部分股份制银行直接停贷。
煤电企业转型的三条可行路径
路径一:从“发电”到“发电+调峰”的角色切换
问:同样一台百万千瓦机组,如何靠调峰多赚一份钱?
答:通过灵活性改造,机组最小技术出力可由50%降至20%,在现货市场中以深度调峰补偿形式获得额外收益。以内蒙古某电厂为例,2023年调峰收入占全年利润27%。
路径二:耦合新能源的“煤电+”园区模式
典型做法:
1. 利用煤电厂蒸汽余热为周边光伏制造企业提供稳定热源,降低其天然气锅炉成本;
2. 在煤电厂闲置灰场建设分布式光伏,所发绿电直供厂用电,降低煤耗3~5克/千瓦时;
3. 通过绿电交易将新能源电量置换给高耗能用户,获取溢价。
路径三:CCUS与氢氨联产的产业链延伸
技术成熟度排序:
燃烧后捕集(MEA法)>富氧燃烧>IGCC+CCS
经济性关键点:
- 当CO₂售价≥200元/吨时,CCUS项目IRR可达8%;
- 将捕集的CO₂用于驱油或食品级干冰,可提升收益30%以上。
氢氨联产方面,国家能源集团泰州电厂已投运亚洲最大煤电CCUS+制氢示范项目,年产氢气1000吨,全部用于园区化工企业。
煤电企业转型的三大风险与对策
风险一:灵活性改造成本回收周期长
对策:优先选择已运行10~15年的机组改造,避免沉没成本过高;同时争取容量电价补偿,缩短投资回收期至5~6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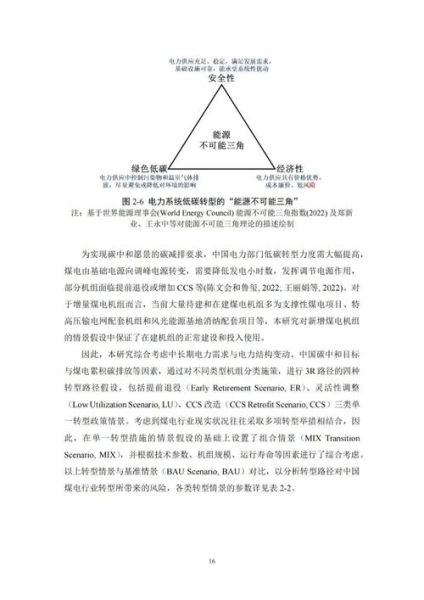
风险二:新能源配套用地指标难获取
对策:与地方政府签订“煤电调峰换指标”协议,承诺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不超过3500小时,换取新能源用地优先审批。
风险三:CCUS技术路线选择失误
对策:小规模试点先行,采用模块化撬装装置,单套规模控制在10~20万吨/年,降低试错成本。
投资者如何评估煤电转型企业的真实价值?
核心指标:
1. 调峰补偿收入占比:>15%说明转型已见成效;
2. 新能源装机权益占比:>30%可平滑煤价波动风险;
3. CCUS项目IRR:≥8%才具备大规模复制价值。
警惕两类“伪转型”:
- 仅将厂内光伏发电量用于降低厂用电率,未产生额外收益;
- 将煤炭码头改建为LNG接收站,但缺乏长期气源合同。
未来五年煤电行业的三种可能情景
基准情景(概率55%):煤电装机峰值出现在2026年,此后以每年1.5%速度退役,转型企业估值溢价20~30%。
激进减排情景(概率25%):碳价快速升至200元/吨,50%煤电机组被迫提前退役,行业出现大规模资产减值。
能源安全回摆情景(概率20%):极端天气导致保供压力,煤电利用小时数回升至5000小时以上,转型进程放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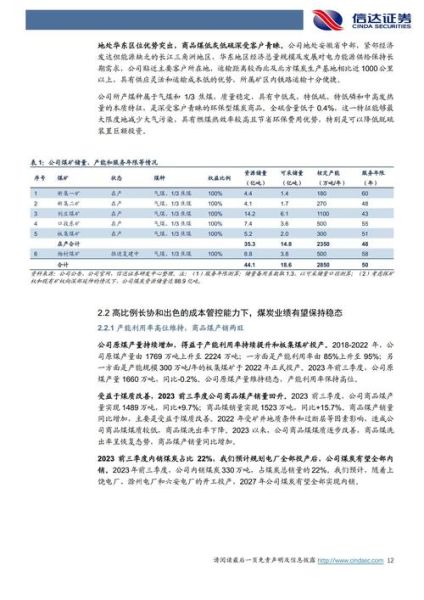

评论列表